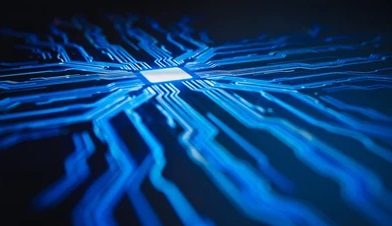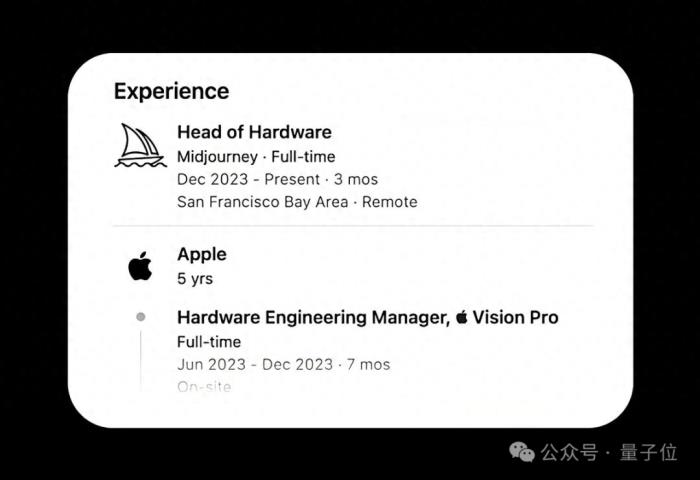如果研究有境界,工程师们需要怎样的工作乐园
2019年首届OPPO未来科技大会上,低调的创始人陈明永公开亮相,宣布未来三年,将投入500亿研发预算,并提出“万物互融时代,将不会再有纯粹意义上的手机公司。我们要抱定10年磨一剑的信念,勇于研发创新的深水区。”
这一宣言,或许是外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OPPO投入底层核心技术的决心。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17年,OPPO已经开始内部动员。
彼时,这家从蓝光DVD起家,经历了MP3/MP4时代,最终深扎手机市场多年的公司,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
那一年,华为凭借搭载麒麟970处理器的Mate 10系列在高端市场中的份额激增400%,取代OPPO,成为中国手机市场新的「一哥」。而OPPO当年出货量仅同比增长2.7%(据IDC 2017年市场监测数据)。
但事实上,正如静水深流,表面平静的下面,一个企业的变革酝酿也往往早于世人的感知。OPPO死磕技术的野心扎根落地,正是如此过程。
2018年4月,OPPO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次,OPPO也决定,让一部分工程师「为技术而技术」。如英国诗人王尔德所言,「art for art's sake」,为艺术而艺术。
1、自发时期:风筝与线
一直以来,OPPO总是被当成一家终端产品公司被世人所关注,另一个少有人知道的事实是,OPPO的标准必要专利数在中国手机厂商中仅次于华为。这显示出OPPO的研发实力不可小视。
卢建强是OPPO科技实力由自发时期进化至自主时期一整段历史的见证者。
2001年,他加入公司,是最早一批加入OPPO的工程师之一。OPPO从视听时代到播放器时代,从功能机时代到智能机,再移动互联网时代,涉猎的创新产品包括音响、DVD、MP3/MP4、电子书、平板手机等等,他或者或少都有参与。
在研发的早期,产品与技术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同事们在一起,经常开玩笑形容,在企业做研究,技术与产品的关系就像风筝与线,技术是高高地飞在空中的风筝,而产品则是地上牵引着风筝的线,给予技术以方向感与安全感。
在卢建强的研发生涯中,他记得与同事们一起经历的高光时刻,印象最深的是作为项目经理,在2011年研发出机身轻薄的Finder,2012年推出体现OPPO浪漫唯美设计的Ulike2极致美颜相机。

与他交流,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作为一位OPPO工程师,他对产品创新的理想与热情。满足产品、「取悦」用户,能够给卢建强等OPPO工程师带来直接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这时候的OPPO,技术创新紧紧贴合产品需求,从产品中汲取灵感,又对产品带来直接的裨益。这也让OPPO穿越多个产品时代,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科技行业,一直是“坐在牌桌上的重要玩家”。
2、自觉时期:达芬奇实验室
科技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和产业间跨界竞争,OPPO面临的主客观环境都已经发生巨变。早先的创新路径开始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OPPO在2012年引进的IBM的IPD变革是技术研发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新成立的技术部将原有的各个分散的硬件、软件与结构等独立分散的小型开发部集合起来,对整个企业的技术研发进行统一管理,以技术平台的形式支撑工程师们去做产品研发。
如果将技术比喻为个体,那么此时的OPPO在技术创新上就相当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逐渐拥有了自主的个体意识。
但这次组织架构的调整,在后续的在运作中发现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此背景下,OPPO尝试将一部分技术人员从产品开发中抽离出来,成立独立的部门,技术作为侦察兵在前面探路,产品作为主力部队在阵地打仗。
2016年,一个探索型的技术组织——达芬奇实验室在OPPO内部应运而生。实验室的主要工作分为两块,一块是技术创新,另一块是技术规划,由在OPPO有多年工程师经验的卢建强出任负责人。
达芬奇实验室成立之初仅有35人。35人的小团队在今天看起来只是一件平平无奇的“部门级”调整,但却是OPPO前沿技术探索的第一步。
达芬奇实验室的工作,既有成功也留有遗憾。
2017年,在巴塞罗那MWC展会上,达芬奇实验室在业内率先发布了5倍光学变焦技术,它是一种全新的潜望式结构摄像头模组。当时做出2000台样机用于测试和MWC展示,没有商用。

这项技术再次被行业关注,是两年后的2019年第一季度,OPPO和华为几乎同时在Reno 10倍变焦版和P30 Pro两款机型上,发布和商用10倍混合光学变焦技术。
SuperVOOC是达芬奇实验室的另一代表作。在研发阶段,也收到了来自公司内部不同声音的反对。
张加亮要做 100W 的闪充,按 5V 算,需要 20A 的电流。当时负责技术的高层一看计划书,就提出了疑问:「20A电流在这么小的PC板里串来串去,不怕电池会燃烧、爆炸吗?」
技术至上主义者有自己仰望的星空,产品开发者却需要脚踏实地。单从前沿技术的维度看,SuperVOOC的概念绝对惊艳,但产品作为最终技术的落地方,必须考虑技术应用的安全问题。
当时听到质疑,卢建强与团队差点就打起了退堂鼓。但转念一想:别人提出疑问,并不一定是反对执行,而是指出挑战,让技术去解决。回归达芬奇实验室成立的初衷,「还是要做正确的事情」,团队坚持去做 SuperVOOC。
最终,「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VOOC快充在2019年迎来了它的升级版本——65W SuperVOOC。2022年2月,OPPO又发布了150W的SuperVOOC快充技术,再一次打破了手机快充的天花板。
达芬奇实验室的经验和教训,使OPPO高层意识到:将技术创新与当前的产品紧紧绑在一起是有风险的。手机是智能产品的终点吗?谁未来会颠覆手机?颠覆者的技术基础是什么?OPPO做好准备了吗?
从研发周期来讲,产品业务面临的半年至一年的档期压力,并不适用于需要长期投入的科研项目。产品研发中所考虑的资源调配原则,也不适用于前沿科技的探索。
技术的问题只能由技术解决。前沿技术的探索,必须将研发人员从原有开发体系中解放出来。
2018年4月,OPPO研究院成立,将达芬奇实验室的原有团队与其余几个部门整合在一起,明确其主要目标是探索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走长期主义路线,与OPPO原有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开发体系彻底分开。
3、自主时期:消灭短期KPI
2017年年底,OPPO内部召开面向未来五年的战略会议,CEO 陈明永在会上斩钉截铁截铁地说「一定要成为研发技术型企业」,随即传出成立OPPO研究院的消息,刘畅担任研究院院长。

得知成立研究院时,卢建强是举双手赞成的。一是前沿科技要有专人探索;二是研究院与产品开发分开,产品开发有自己的专家团队,不必再分散精力去解决产品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三是消除了工程师要在短期内出成果的焦虑。
创新者的春天要来了。但在这春风吹拂的土地上,技术者要耕种些什么?
刘畅记得,研究院成立前夕,陈明永与另一位高管曾元清分别找他谈过话,问出同一个问题「你打算做什么?」
刘畅在2008年加入OPPO,先后担任过硬件技术部和手机软件部负责人。严格来讲,刘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因其在硬件技术、软件技术与产品研发上均有历练,对前沿技术方向的把握有自己的见解。
在科研规划上,他诠释自己的角色,无非两点:一是保证研究院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两个战略性前瞻研究方向。二是营造出前沿研究的环境,找到合适的技术人员,让技术人员去自由开拓、探路。
最开始,OPPO研究院提出五个大的方向:AI、IoT、影像、标准与新形态。2019年升级为「3+N+X」,其中「3」指硬件、软件和服务三大基础技术,「N」是长期构建的若干个能力中心,包括人工智能(AI)、安全隐私、多媒体、互联互通等,而「X」指OPPO的差异化技术,如影像、闪充和新形态。
在研究院自由探索的氛围下,很多和OPPO当前主营业务无关的科研课题得到了自由成长的空间,如 XR,甚至是机器人与自动驾驶。
但,OPPO研究院的终极目的不是成为技术的拥有者,而是打造技术货架,成为最佳用户体验的解决方案提供者。
为了支撑这一目标的达成,OPPO研究院设立了“Lab、STG、Platform”三种形态的创新组织。
其中Lab是最小的研究型实体组织单元,每个Lab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但每个人都是该领域的技术专家,针对一个技术方向进行攻关;STG特别技术小组,面向未来新机会,围绕特定场景,通过技术先行探索战略性新业务方向布局,孵化创新原型或解决方案;Platform则是工程化技术平台,面向Lab和STG,打造创新原型,实现技术转化。
整个组织专注在未来 3-5年的技术研发,不必背太多短期KPI。
没有短期KPI,工程师们迸发出更多灵感,卷轴屏概念机、饼干充电器、AirGlass等具备行业性颠覆创新的产品均出自研究院工程师之手。
让前沿技术脱离产品,但牵引的线从未消失,只是主体由产品变为了OPPO。
4、自由时期:工程师乐园
在对研究院的管理上,刘畅强调「长期主义」,取消半年一度的考核、改设年终综合评价。这听起来颇具吸引力,毕竟这两年在互联网大厂里,连科学家也要「开始学会赚钱」。
而刘畅却对笑谈:「我现在唯一的 KPI 就是必须把钱花出去。」
在对技术人员的「管理」上,刘畅谈到最多的一个词是「自由探索」:「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负责对接资源,给他们创造自由探索、积极创新的环境。」
除了给予足够的资源,打造工程师乐园的关键是:决策充分基于对技术Know-How的尊重,充分融入工程师的好奇心与创新。
OPPO研究院对工程师们的创新项目,给予更大的容错度和包容。不光要权衡一个课题的研究价值是高是低,还要保护工程师们做科研创新的热情和好奇心。
负责 “人参果算法”(一种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的谢红斌在2018年11月加入OPPO研究院。此前他在上海的陶氏化学工作,对OPPO的认知一度只是“擅长营销”的公司。
一个中秋节的晚上他接到了张加亮的电话,邀请他去深圳面试。谢红斌很惊讶,没想到行业里泰斗级的人物会亲自找他。于是,他精心准备了十几页技术文档,从上海飞去深圳。
见面后约在一间咖啡厅里,张加亮并没有看这份文档,就着行业内行业外谈天说地,还跟谢红斌聊了许多诗与远方的话题。回忆过去,谢红斌仍被张加亮的谦虚和没有一点架子深深打动。
谢红斌加入张加亮带领的电源研究实验室,担任材料应用工程师。他进入团队后,一直负责研究电池材料与算法。该课题虽然属于电源技术的范畴,但与OPPO已经成名的闪充技术不同,是在算法层面与电池内部大做文章,是完全未知的、全新的方向。

“人参果算法”是谢红斌研究了三年多才取得的成果。它的神奇之处是可以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根据每块电池的状态自动调整充电进度。充放电循环从800 次提升至1600次后,电池容量依旧大于80%,大大提升了电池的寿命。
事实上,延长手机电池的寿命并不是谢红斌一开始探索电池算法的目的,只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可以用来提升电池的寿命,有用户价值便推向商用。
人参果算法的成功,验证了坚持长期主义做前沿技术研发的可行。在去往终点的路上,随时会有沿途的惊喜。
倡导长期主义的研究风格尽可能地使工程师的创新压力降到了最低。「研究院里,每个人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你做任何研究都不会有人阻挠你。」谢红斌总结。
2020年9月加入OPPO研究院担任热设计工程师的胡院林则认为OPPO研究院是“工程师乐园”,他这样总结他在OPPO研究院的工作体验:相比于科研机构,离技术落地运用更近,又远离了产品短期KPI的压力。
而这也是OPPO研究院吸引科学家和年轻人的法宝。在刘畅看来,OPPO十几年来在产品和工程上的积累保证了从创意到产品的完整交付能力,使得科研人员的想法得以更好地落地;但在前沿探索上还存在很多没有基础的新领域,所以研究院愿意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自主探索。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OPPO研究院将年轻人文化打造到了极致。相比起外企,这里年轻人更多,更有激情,做事也更直接,更纯粹。
作为一家崇尚技术的公司,在OPPO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管你是做什么职位,同事们默认对你的称呼一律是“X工”。
优秀的硬件基因、稳定的营收支持、自由的科研环境,为OPPO研究院吸引了大批科研人才。过去四年,OPPO研究院的规模已经由最初的不到50人增加至接近1000人。公开资料显示,今天OPPO研究院在闪充、5G标准、计算机视觉、语音语义、电致变色材料应用等技术领域已经处于世界第一梯队。
“选人进来后,不要让人家受挫。”刘畅最后总结。在他看来,研究院未来能源源不断输出像SuperVOOC闪充这样的超级技术并将其落地应用,不完全是靠高管指明方向,而是靠工程师的自动自发和从下至上的推动。这些激情、活力,匹配上恰当的自主、自由机制与氛围,假以时日,OPPO或许可以率先在国内打造出真正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工程师乐园。
- 免责声明
- 本文所包含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新火种的观点。在新火种上获取的所有信息均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新火种对本文可能提及或链接的任何项目不表示认可。 交易和投资涉及高风险,读者在采取与本文内容相关的任何行动之前,请务必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最终的决策应该基于您自己的独立判断。新火种不对因依赖本文观点而产生的任何金钱损失负任何责任。
热门文章






 新火种
2023-10-29
新火种
2023-10-29